


2022年8月31日
今天读《知行合一王阳明》这本电子书,一口气读了整本书的15%之多,这是对他的前半生的记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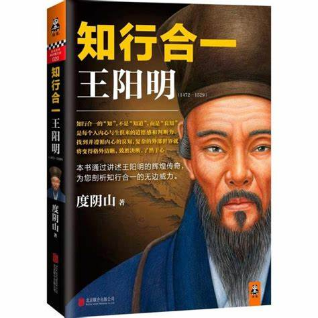
通过阅读,我看到了王阳明的孩童时代的兴趣广泛(不学无术),让父亲操碎了心;体会他的“读书做圣贤”为第一等事的鸿鹄之志,和他“经略四方”建功立业流芳百世的伟大理想;佩服他专注兵法独自入蒙的勇气、新婚失踪求道术的痴迷,践行“格竹子”质疑朱熹理学的“格物致知”;惊叹于他在军事、道教、佛法和辞章上的造诣;感叹于他在“仕途上”的失望和在求佛道中渐悟:“亲情与生俱来,如果真能抛弃,就是断灭种性”回归世俗亲切;通过劝导和尚回家,领悟:无论多么宏大深渊的宗教,在人性面前都要俯首称臣。
王阳明在佛教领域多年的浸染和探究,终于在最被人忽视的人性上看穿了佛教的弊端。正如他创建心学后所说的,佛教是逃兵的避难所。佛教徒所以出家,就是想逃避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朋友这五伦中他们本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。
更是十分佩服他的“洒脱”:什么是洒脱?王阳明用他的行为告诉了我们:该放手时就放手,不必计较付出多少。王阳明在辞章、道教、佛教上的付出如海洋般深沉,在这三方面的成绩几乎是他半生的心血。然而,他一旦想明白,说放就放,连个犹豫的眼神都没有。王阳明用他和辞章、佛道的一刀两断指出了一条心法:只有放弃,才有日后的得到。如果你在付的人事上得不到快乐和人生价值的 答案,他就是一个包袱,甚至事五行山,只有放下他,才能轻装上路,继续你的前程。
然而,王阳明也有他的不甘和困惑。在读到王阳明重归理学前的一次拷问时,不知为什么,我竟然一度泪目,被戳到了“痛点”……
主持山东乡试时,他问考生:“合格的臣子以道侍君,如果不能行道,就可以离开君主(所谓‘大臣者,以道侍君,不可则止’)?”这是孔孟思想的精华,要求臣子要以忠诚之心对待君主,可如果君主对这份忠诚视而不见,那就应该离开。这不但是一个臣子应该具备的品质,也是“圣贤”的素质之一。
他大概是想通过这样的试题来求证,如果一个臣子没有机会没有平台施展自己的抱负,是不是可以转身就走?自己这么多年来在工作和隐居之间的华丽切换是否正确?他还想知道,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毫无条件地忠诚领导还是只忠诚于真理。
其实他的答案就是考题本身。王阳明几乎用大半生时间在践履这个答案,就是在这时,他心中已经有了心学的种子:我只对自己的心俯首听命。但是,王阳明还是希望所有的臣子以道侍君时能被君主关注,因为“不可则止”听上去很潇洒,对于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而言,却是痛苦的。
就是这句话,看着看着,泪眼模糊……
我在想:被碰触“泪点”,是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心境吗?只有自己的心知道吧。我想“不可则止”这是对于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而言,都会有过这样的痛吧!
王阳明又问考生:“佛道二教被人诟病,是不是它们本身的问题?”他的答案是,佛道二教本身没有问题,有问题的是弘扬佛道二教的那些人。道教说能让人成神,这太荒诞;佛家说能让人成佛,这更无稽。即使它们真的可以让人成神成佛,付出的却是抛弃人伦的代价,这种神佛不成也罢。
所以他和佛道一刀两断。
最后,他站在了朱熹理学前,对考生说:“天下之事,有的貌似礼但实质上不是礼;有的貌似非礼但实质上就是礼。”二者的区别很细微,如果不用心去研究(格)它们,将会产生大困惑,就不能得到真理。
这是他否定辞章、佛道后重新回归朱熹理学的一个表态。他两次倒在理学的“格物致知”上,但还是认定人人都应该“格物致知”。
山东乡试结束后,王阳明登了泰山。在泰山之巅,他写了几首诗。诗歌是沉闷抑郁的,他说自己的使命感没有实现的机会,他又说自己虽然认定佛道并非圣学,但朱熹理学也没对他笑脸相迎。他还说,半生已过,往事不堪回首。
这是王阳明对他的前半生做了一次严肃的回顾和总结。虽然,自己没有王阳明的造诣和成就,但回想自己的前半生多少也有些共鸣吧!
接下来的篇章是王阳明致力于儒学和心学的悟道,也正是我想学习和修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