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要说,孔子有弟子三千,芝兰玉树满庭阶,他最喜欢谁?
如果仅从《论语》字面上看,应该是颜回了。其二十篇中,直接提到颜回的,我数来有二十一句之多。这二十一句中,孔子没有一次批评过颜回,几乎都是夸赞,夸赞到过分处,如仰天人,都不像一位老师对其弟子的夸奖。而对其他关系亲近的几位弟子,或多或少都有过批评,或指出过他们的不足。
1
孔子对颜回的赞美简直无以加复
想那颜回,少年时随父进入孔门,眼前所见每一个人都比他大。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,他难免青涩,腼腆,师长前头不敢言。孔子对这个寡言少动的小孩子开始不大注意。不久之后,他就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,其实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愚钝:
“吾与回言,终日不违,如愚。退而省其私,亦足以发。回也不愚。”
一个人的聪明,孔子当面看不出来,只有等到离开之后回想起来时,才能品味出来。那这个人是怎样的聪明呢?何况颜回只是一个孩子。也许只有孔子那样敏锐善察的老师,才能觉察到颜回的天资过人。
随着相处日增,过了一段时间,孔子对颜回的印象又加深了一层:
“语之而不惰者,其回也与!”
在所有听课的弟子中,能做到一直毫不懈怠的,只有颜回一人。而这个“坚持不懈”,恰恰是孔子对学有所成最看重的品格,孔子自己也是这么坚持过来的。所以从这时起,孔子在内心里,应该是非常看好这个孩子的未来了。
观察一个人,光有韧性还不够,还得看志向。有次孔子让几个弟子各言其志,随意考察他们,唯有颜回说“愿无伐善,无施劳”,即不自夸,不表功。颜回年轻时,就懂得这样的收敛,没有和其他弟子那样张狂外露,实在不符一位少年应该具有的意气。这应该与他独处于父师长辈与礼教的环境之中有关,环境促使他少年老成。而少年老成,在孔子这里被认为是好的事情,相比其他弟子,孔子不吝赞美地说:
“回也,其心三月不违仁,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
而“仁”,是孔子理想中的最高境界。在孔子的眼里,只有颜回最接近这样的境界,颜回可以做到长期不偏离仁德,别的弟子(甚至包括孔子自己),都不行。
颜路住家离孔子家不远,对于颜家的落魄与穷困,孔子早就知道。但在家访过颜回的生活情况后,孔子是一句三叹地称赞颜回道:
“贤哉!回也。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!回也。”
也就是说,在孔子那里,颜回的穷,竟被说成了是一种美德。甚至后来,孔子还要借用颜回的人生态度来讲述他自己的人生追求:
“饭疏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。”
这样的讲述,对在生活上十分挑剔、习惯了养尊处优的孔子来说,显然有点虚假。但他能如此屈尊去效仿一个穷学生,亦是难得,亦不寻常。
综上可见,孔子对颜回的喜爱——在客观上,是叫赞美——是不是达到了无以加复的程度?他的赞美,他的称颂,弟子无人不晓,鲁国君臣皆知。事实上类似的赞颂肯定不止《论语》上由其弟子们记下来的那点。
那么我要问,孔子对颜回的喜爱,是真的喜爱吗?孔子是单纯地从内心、从师徒的感情上去喜欢颜回的吗?
不是的,我觉得不是这样,越读《论语》,我越是从中感觉到有极大的悲哀,那些悲哀难以明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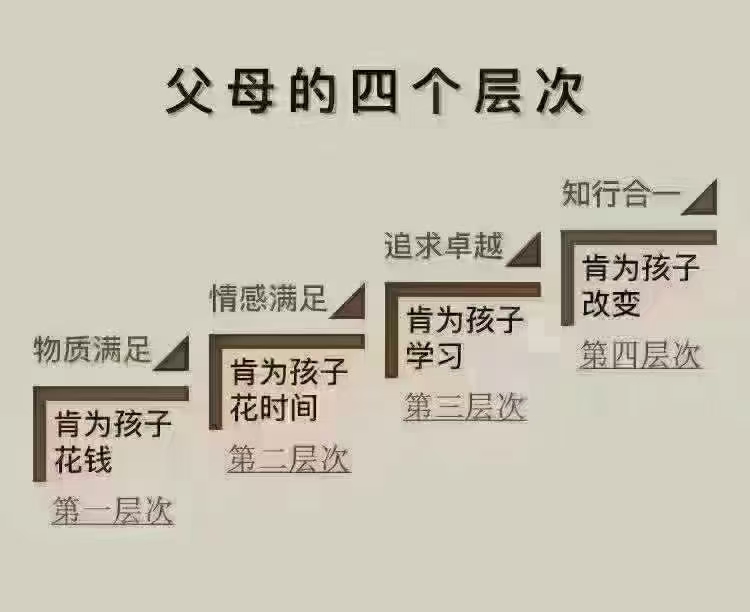
2
聪明的颜回没有去谋生路,居然穷困而死
颜回的穷困,和颜回的聪明一样出名,甚至更为出名。
历代之人每谈穷困,都会禁不住学着颜回自我解嘲: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”,这样虽穷,却也如达人,并不可耻。
但问题是,颜回既然那么聪明,却又极度贫困,二十几岁就白发苍苍,不到四十岁就穷困而死,这是不是非常矛盾,很不正常?难道孔子讲的“学也,禄在其中矣”,或者子夏讲的“学而优则仕”,都是假的吗?难道“七十二贤之首”连找碗饭吃的能力都没有吗?
首先来看,是没有人请颜回做官吗?这肯定不是。连那些学问远不如颜回的弟子都纷纷被人请走做官做臣,连子路这样做学问未能“登堂入室”的人都是楚国屡求不到的将帅之才。谁能请到七十二贤之首的颜回,绝对是该国当朝或某大夫家的莫大的荣幸,怎么会没有国君权臣想请颜回去就职呢。
即使没有人请颜回去做官,有孔子和那一大帮在诸侯国间能呼风唤雨的同门师兄弟,颜回还愁没有官做吗。子路不是没有禀告过孔子就悄悄把又憨又矮的子羔送出去当官吗。
事实上,孔子经常向君主大夫们推荐他的弟子去当官,比如什么“由啊”“赐啊”“求啊”“赤啊”等等,或是弟子们之间经常互相推荐。但是,就是从来没有看到,在颜回活着的时候有人推荐过他去当官。等到有人终于愿意开口向君主大夫们推荐颜回的才能的时候,竟都是在颜回已经死了之后。而那个屡次推荐颜回的人,就是孔子:
哀公问:“弟子孰为好学?”孔子对曰:“有颜回者好学,不迁怒,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……”
季康子问:“弟子孰为好学?”孔子对曰:“有颜回者好学,不幸短命死矣!今也则亡。”
……噫欷吁!颜子地下有知否?他生前没有获得老师的举荐,死后老师却为他屡次大开金口——然而这时有什么用呢。
那是颜回生前鄙视做官、不想做官谋个好出路、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吗?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,颜回非常清高。就如《庄子》中所记:孔子也曾问颜回“家贫居卑,胡不仕乎?”颜回说他家有田近百亩可以自足,学夫子之道可以自乐,所以“不愿仕”。
可这不是胡说吗。颜家若有田百亩,又怎么会“家贫居卑”,最后穷困而死呢?陶渊明隐居时也老哭穷呢,可他家三代官宦,祖田遍眼,那叫穷吗?颜家的穷是真穷,陶家的穷是假穷。
孔子的一大癖性,就是嫌弃弟子想以种植为业。孔子更不会教弟子不要出仕(除了为虎作伥、为奸作祟、不仁不义外),他是鼓励弟子们“待价而沽”的,要做上层君子,而不是下层鄙人。
同样困苦面黄肌瘦的老庄这么编,肯定是看到颜回一生“甘于穷困”,就想强拉颜回为心灵知己,为他的“逍遥”“无为”作证吧?
颜回不想做官吗?不是的。我认为:颜回其实也想做官,颜回岂会没有一点想做官的想法。世上有哪个人愿意放弃唾手可得的温饱不要,而要让全家人去承受饥寒交迫的痛苦?
颜回也曾和其他弟子一样,怀着内心的梦想,向孔子认真请教过入仕为官的学问:
颜渊问为邦。子曰:“行夏之时,乘殷之辂,服周之冕,乐则《韶》舞。放郑声,远佞人。郑声淫,佞人殆。”
既然,孔子那么赞美颜回,可他为什么不赞美颜回有入仕为官之能?或有经商货殖之能?或有教书抄写之能也行啊?这对颜回来说是小菜一碟吧。可孔子唯独称赞的,是颜回的勤奋博学与谦忍尊师,因为勤奋是孔子所需的,谦忍也是孔子所需的。

3
探究颜回穷困而死背后的悲哀
颜回生前,为什么没有获得孔子的举荐?或者即使没有孔子的举荐,他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求职做官?或者他像子贡一样,去曲阜古街边做点小买卖谋生也行啊。颜家的生活那么穷苦,他做个买卖,凭他的名气与才气,和同门的帮衬,绝不至于让全家受饿吧。说不定他会和“北大屠夫”陆步轩一样咸鱼翻身,发达起来重回先祖的贵族地位。那对颜回来说,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
事出反常必有妖。
颜回之所以没有做官或经商,其实就与孔子有关,因为孔子,颜回一生都没有机会去做官,或谋生。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判断呢?只要来看看颜回的一生中,主要干了些什么事情就知道了。颜回的一生并不复杂,相较于其他弟子,很简单:
孔子二十七岁开始办学,那一年颜回刚好出生;
孔子四十岁时,颜回十三岁,开始随父进入孔门听学;
七年之后,孔子四十七,“不仕,退而修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”。那年颜回刚好二十岁,开始跟随孔子整编《六经》,游历各国,很少分开。
颜回的出生,好像就是上天送给孔子从事文教事业的礼物,就像哪咤诞生下来辅佐姜太公一样。从二十岁时起,到四十岁之前终,颜回的一生好像就干两件事:在家是孔子最得力的编辑,在外是孔子最得力的侍者,一直陪伴着孔子。
孔子凭借着一种无形的力量,一直将颜回紧紧留在身边。那种力量是什么?就是赞美!是独一无二的赞美,是不可替代的赞美。如果说出外游历还有人可以代替,比如子路,孔子就曾说,“乘桴浮于海,从我者其由与”。那整编《六经》,就没有人可以代替颜回了。颜回的聪明灵悟,知识渊博,无愧于他是七十二贤能之首。而更重要的是,颜回的尊师顺从,从不违逆,也是孔子最看重的地方。没有一个弟子,能像颜回那样恭敬,顺从,听话,即使知道老师错了,也从不正面说出老师的错误,都在内心默默消化干净。
这样好用的学生,孔子不把他留在身边,帮助自己完成编著的理想,孔子还能留下谁呢?即使后来孔子临死之前,他的病床旁边呆得住的陪护,也不过一两位弟子而已。无论鹰、雀,长大了,翅膀硬了,总要飞出去的。
孔子是一代圣师,他当然不能用威严的命令要求颜回,更不能用现代所谓的“PUA”办法控制颜回,让颜回机械地服从。孔子唯一的办法,就是赞美,赞美,不断地赞美。只有通过赞美,才能让颜回无法离开他的老师,因为在老师那里,在伟大的理想面前,颜回是不可替代的,他是不能离开的。
又比如,“子罕言利,与命,与仁”,孔子很少谈到利益,却赞成天命和仁德——这不就是用来对待颜回的最好的办法吗。
然而孔子真是一个“罕言利”的人吗?也不是。如果有人想求教于孔子,又不带着“束脩”,孔子随便是不会搭理的。阳虎有求于孔子时,就给孔子送上过一头熟乳猪,作为利诱。
但是在留住颜回的年月里,孔子可能就“罕言利”了。
我猜想着,颜回陪伴孔子近二十年,很可能是没有工资补贴的,有也不多。因为他的身份,始终只能是弟子,而不会是仆佣或家臣。颜回以弟子之礼服侍老师,应该是名正言顺,没有工资的吧;拿了工资,那就是违礼的吧?而违礼,是孔子最忌讳的事情。
同样是贫家弟子,原思给孔子家当总管,孔子都知道给原思俸米九百,原思推辞不要,被孔子制止。但是颜回,每月能得到多少的生活补贴呢?真是不敢想象,因为颜回的穷困,一直摆在那里,就没有真正得到改善过。
这或许才是善良的颜回,只能穷困而又不能脱身离去的原因。
颜回把自己的一生,献给了孔子,献给了《六经》事业,甘愿做孔子书房中那个默默无名、受尽清苦的“扫地僧”。
那么孔子是怎么回待颜回的呢?工资补贴的事是没法实据考证了,那就看看颜回死后,孔子是怎么对待他的。
颜回因病而卒,在孔子眼里,“礼不下庶人”,一个没有大夫身份的贫民,没有必要给予隆重的安葬,让颜家随便埋葬就行了。可是颜家实在太穷,连棺椁都无力置办,难道要让颜回草草抛尸荒野?这下颜回的同门师兄弟们不干了,他们凑钱买了棺材,又请求老师拿出马车,以车为椁运送棺材。但是孔子不同意,这位曾经无尽赞美颜回的老师说:以马车运送棺材,那是大夫死后才能有的待遇,运送颜回就违礼了,不行,不行!
孔子的弟子们第一次愤怒了,颜回是因为谁、因为什么事业而死的,他们难道不清楚吗?他们竟然不顾老师的反对,仍然拿孔子的马车去送葬颜回。
孔子没能阻止弟子们,当时哀叹道:这不是我要越礼啊,是弟子们要这样干的。孔子哀叹的不是颜回的死,而是他的那一套阶级礼法。
可怜的颜回!死后的送葬队伍里,没有那个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人。
4
结束语
当孔子对颜回不尽赞美时,可否知道背负着这个赞美的无限孤独和伤感。
当我们现代人翻阅《五经》、吟诵《诗经》时,可曾知道那一页页纸卷里面,也凝聚着颜子毕生的精血。
我还想到一件事:
有次孔子的车队逃出匤地,颜回是最后一个逃出来的。孔子看到捡回一条命的颜回,他直不愣蹬地对颜回说: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。颜回的回答是:你还活着,我怎么敢死呢!
